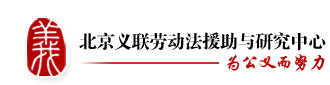七份胜诉判决为何不能保障工伤先行支付权利?
“我下一步该怎么走?”自从在工地上受伤以来,袁师傅一次次向社保局,向法院,向律师,向记者问起这个问题。七年过去了,他的问题却陷入了一个不应有的怪圈。
2008年,袁师傅在乌鲁木齐市三师建业劳务有限公司务工时受伤。拖着伤腿奔波近两年后,袁师傅于2010年3月被认定为工伤,鉴定为七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的拖延和法律程序的繁琐,到2011年7月,案件终于进入执行程序时,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三个月后,法院作出了裁定书,中止执行。
作为义联的咨询专员,我第一次接到袁师傅的电话是在2012年。那时,他刚刚拿到第一份行政诉讼胜诉判决,社保局提起了上诉。
袁师傅提起行政诉讼的依据是《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2011年11月30日,袁师傅向乌鲁木齐市社保局递交了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一个月后,乌鲁木齐市社保局作出不予先行支付的决定。被拒绝后,袁师傅开始进行行政诉讼。一审法院支持了袁师傅的诉讼请求,责令社保局六十日内向袁先生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社保局不服,提起上诉。
听完袁师傅的叙述,我很是吃惊。《社会保险法》从2011年7月开始实施,工伤保险先行支付是其中的新规定。袁师傅依法提出申请时,该法实施不到半年,许多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尚不知先行支付为何物,而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伤职工,迫于无奈,已经开始拿起崭新的武器主张自己的权益,并一步步坚持下来。袁师傅拿到的胜诉判决,在新疆地区尚属首例,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令人振奋的先例,可以说,给广大亟待救助的未参保工伤职工带来了希望。
然而,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始,却慢慢演变出了一个尴尬的后续。
拒绝支付是不是履行职责的一种方式?
2012年11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作出这一裁定的理由是:社保局就袁师傅的申请已经作出答复,该答复本身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原审法
院以不作为类案件进行审理有误。
这个裁定,决定了此后法院处理袁先生一案的逻辑:社保局作出答复,就是履行了义务,至于履行恰当于否,是另一个问题。
这样的逻辑,源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判决类型的分类,其中有两类易于混淆的判决,履行判决与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即法院查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撤销判决,即行政行为有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的,法院判决撤销,同时,法院可以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予先行支付的答复算不算对法定职责的一种履行呢?如果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法院作出的,就不会是履行判决,而会是撤销判决。
袁先生不得不重走一遍一审、二审程序。2013年5月17日,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社保局的答复,责令社保局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无奈的重作判决
如前文所述,法院在作出撤销判决的同时,可以一并作出重作判决,即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在袁先生的情况中,法院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如果事情按照理想的情况发展,袁师傅虽然绕了些远路,最终还是可以走到目的地的。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如人意。二审判决作出四个月后,社保局作出了姗姗来迟的答复,仍然拒绝对袁师傅进行先行支付。而拒绝的理由,与此前大同小异。
这是行政重作判决所面临的尴尬。法院的生效判决,没有直接要求社保局先行支付袁师傅工伤待遇,只是责令社保局重新答复,但是,在判决理由中,法院明确阐述了撤销原答复的原因,并说明社保局拒绝支付的理由不能成立。在一个行政权对于司法权充分认可的环境中,这样的判决已经足以指明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方向,司法权不直接干涉行政权,行政权也充分尊重司法权,二者协调运行。然而,社保局的答复明明白白地显示,这样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
法治观念的普及其路漫漫,那么法律的强制规定又如何呢?《行政诉讼法》明确,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
同的行政行为。且不论大同小异算不算“同一的事实和理由”,袁师傅发现,即使行政机关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事实和理由,他也没有快捷的救济途径。社保局已经作出了新的答复,认为答复不合法,他似乎只能再次进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绕远路”成了“兜圈子”。再走一次程序,结果可能还是一样,到时又怎么办?虽然心里没有底,不甘心就此放弃的袁师傅还是又转向法院寻求帮助。
救济之路条条碰壁
只要求重作的判决,遭遇了社保部门的对抗。袁师傅希望,法院能作出一个更直接的判决。重作判决是简单地发回重作还是指示重作,即法院是否可以在重作判决中对如何重作直接明确,法律并没有规定,袁师傅想要争取一下。事实上,在重庆首例工伤先行支付行政诉讼中,法院作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指示重作的判决,撤销被告医保局作出的不予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函,同时要求医保局六十日内审核并发放工伤保险待遇。
另一方面,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相关规定处理,比如,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袁师傅也向法院提出了这一请求。
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审、二审。2014年6月10日,法院二审判决,又一次撤销社保局不予先行支付的答复,责令六十日内重作,但同时驳回了袁师傅要求判决社保局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诉讼请求。
社保局似乎已经“驾轻就熟”,临近两个月,2014年8月8日,又一纸答复飘然而来,同样的理由,同样的答复:不予先行支付。
距离受伤已经过去六年的时间,袁师傅拄着拐杖,又站在了维权道路的原点上。在电话中他提起,当初用人单位曾经提出调解,但是数额太低,他没有答应。没有想到走到今天,一分钱也没有拿到。一条伤腿,换来的是纸纸空文。
如果当初答应那个明显低于法定标准的调解方案呢?我没敢问出口,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如今似乎已没有选择,不久,袁师傅又提起了行政诉讼。
2015年3月9日,一审判决;
2015年6月18日,二审判决。
撤销不予先行支付的答复,责令重作。
又一个圈走过。当行政机关发现傲慢与冷漠的成本只是一点点参加诉讼的时间,还有什么能打破这个圈呢?
我们常常说,普通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差,维权能力弱,或是怯于维权,或是行为过激。但在袁师傅身上,我没有看到这些。七年的维权,在那个领域里,他比多数人都熟悉法律;一次次诉讼,他也证明了,他比多数人都相信法律;在每一次交流中,我都感受到他的坚忍。据说,人们指出不幸者的不足,是为了获取安全感:只要足够努力,做得足够好,就不会遭遇这种不幸。而袁师傅的经历时时诉说着,面对行政权力时,这种“安全感”是多么的脆弱和荒谬。(作者系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公益律师)
本图文系义联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杨藜)
- 上一条文章: 从“美人计”讨薪看农民工维权的法律困境
- 下一条文章: 用人单位拒出庭,劳动关系确认要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