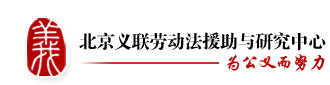无名星座——写给义联的同仁
你是无名星座,只有夜晚,我能够看清你,你能够看清我。无需诉说南风吹落的欢乐。晨曦伴随着寂寞,守护着无边银河。
——题记
小序
每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飞向大地时,我已乘坐北京的城铁[1]上准备在8:30之前赶到一个叫“义联”的法律援助中心上班。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这时的我总在思考这座城市的价值,进而会联想到生活在这座城市并为自己理想奋斗的年轻人。其实说他们为自己奋斗并不一定准确,但因为这座城市有了这些被称之为“北漂”的年轻人,才彰显她古老、经典背后的现代和活力。
义联是专门为劳工服务的公益组织,她的部门建制在同行中算是一流了。我在这里无意于赞美她辉煌的成就,因为我也许还不够资格。但我很想谈谈这里“不一样”的年轻人们,尽管他们是普通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朝夕相处。
一、萤火虫的光
年轻人在一起总是很热闹。中心有很多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精彩。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奉献”。在中国,从事公益事业很难,不会有更多生财之道,也很难跨入“上流社会”。年轻人从事公益便少之又少。但是义联却有一群不一样的年轻人。
李洪波,巾帼不让须眉的援助律师,上过报纸,算是名人。她就坐在我旁边,每天总是忙忙碌碌,很少正点下班,当然也有时不正点上班。她有接待不完的当事人,有应接不暇的卷宗,有堆积如山公文。不仅如此,还要对诉讼组承担协调指导工作。她每件工作都兢兢业业,细致认真,处理了很多疑难案件。面对异常艰难的援助工作我不清楚是什么支撑着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女律师。我想也许是对那份公益事业的热爱吧。
刘升期,术业有专攻,在劳动法方面绝对是“一哥”、“专家”。凡有不决之事,询问这位专家,必能找到答案。他对工作是极其耐心的。无论面前坐着多少当事人,无论当事人有多少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否“靠谱”,升期都会耐心解答,他让我理解到“平和之心是做好法律援助的基本”。另外,升期很爱书,很博学,至少在这点上我们能找到一些共鸣。
韩世春,安徽人,公益律师,我直接“上级”,耐心细致,做法律援助很有宏观性。每临大事而不乱,总是把集体劳动案件处理的井井有条。总结的方法又方便实用。韩律师,也是北漂,也有理想,默默奉献。
中心的人员很多,人来人往,都在为这份公益事业尽自己的努力。不论是即将离职的忠意,还是刚刚入职的伟涛、生林,还有赵律、曾律,不论是工作时间长,还是短,他们都为公益事业奉献着青春和热情,他们都值得尊敬。法律援助要比其他法律工作所付出的劳动难得多,因为面对的受援人群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有的时候,当事人对法律的规定理解比较狭隘甚至偏执,我的同事们总是和风细雨,动情入理、不厌其烦的解释说明,总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为案件比较多,所以加班又总是常事,尽管辛苦,但是快乐。
我总觉得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作用不仅仅是处理个案和维权,更重要的是重建一种社会信任和理念。让无助的人感受社会的关爱,从而信仰法律。让失望的人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为真理而斗争。勇于担负起这份责任,才会使我们工作更有意义。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是什么大律师,但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光和热。,尽管这光如萤火虫一般渺小。
二、有所为,有所不为
坦白的讲,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点浅薄的理解。几年前的六里桥,几个年轻人怀揣同样理想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劳工维权的组织——义联。几年来义联人把这个品牌做大做强了。我想当初他们成立的这个援助中心时,就意味着现代法治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并非所有人都能共享法治的成果,因此有人需要援助;也意味着诉讼需要成本,贫穷难进法院的门;还意味法律与经济的脚步有些分离。今天我想说的是,义联的法律援助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想法:
(一)做个桥梁。中国法治走到今天,确属不易。但一直令我困惑的是,民众对法律的非理性理解和狂热背后的指责。当纠纷发生时,他们也懂得用法律“说话”,甚至不分情况,认为法律无所不能,法律想当然地保护他们。而当纠纷已脱离法律的界限或是非法律原因而无法保护他们时,又会遭到他们无端的指责和批评,甚至是过激。比如咨询人一味地认为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而因证据不足没有被确认,就会认为法律百无一用,牢骚满腹。这种民众对法律理解的冰火两重天是十分危险的,也是“良法”的悲哀。我一直认为中国法律目前来讲,算得上门类齐全,基本完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法律与普通民众之间缺乏一道沟通的“桥梁”。为什么面对“药案”我们会用欢呼的方式送别同类?为什么只要出现问题总会有人出来喊 “法律”不完善?法律制定出来不能束之高阁,需要被民众理解。作为法律援助者希望能够尝试建立这种沟通的桥梁,把法律本来的精神和方法传递给民众。这种桥梁可以熄灭民众偏执的“愤怒”,可以缓解法律的陌生,让法律被理性的信仰。
(二)做个传播者。沟通与传播不一样。前者是让民众理解法律背后的价值,从而变得理性地看待法律。后者是让民众知道法律,从而懂得用法律,及时维护权益。在平时工作中,我总会遇到一些因时效过期而丧失保护利益的案例。这时候援助律师会爱莫能助,劳动者会很失望。如果劳动者能稍微知晓一些法律常识,如果稍微能提高一些法律意识,就不会出现丧失胜诉权的情况。历史不容假设,但可以被创造。我十分看好,晓亮、忠意向农民工普法的项目。法律不仅要进工棚,而且要进社区、学校、工厂。尽管短时期效果不一定显现,但我坚信长期努力必然带来可喜的成果。
(三)完善援助程序,更多的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很同意朱苏力[2]先生的观点最需要法律援助的是那些离法律更远地方和那里的人。北京是劳动法实施最好的城市,更多的取决于政治原因。许多地方就不禁凄然。那里的人得不到援助。能够得到帮助的大多是靠近城市的人。所以有条件的话可以送法下乡。
另外,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纠纷没有什么善恶之别,对错之分。有时,纠纷仅仅是纠纷。还有一些是在利用法律援助,不断的纠缠,甚至“恶诉”。这样浪费了司法资源,挫伤了援助队伍的热情。面对这种情况,我真的很想说“不”。
如何解决,我还未及思考,也很难有机会思考。但我建议同仁门可以从建立严格的评估机制和完善程序两个方面考虑。
义联的法律援助事业,见证了近10年来中国劳工立法进程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立法、守法等环节在中国所引起的深刻社会变革。义联的宗旨没有变,义联人的追求没有变。义联同中国法治一道成长。
三、不可能的告别
过几天就要离职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离职并不意味我不在关注法律援助。我将一如既往的热爱公益事业,尽所能地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所以才是“不可能的告别”。
在义联工作的日子可能不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但却是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我也曾为劳动法规纷繁浩杂而感到烦恼,也知道工伤保险条例并不一定有诊治工伤的良方。午夜加班归来,打开房门,打开电脑,也会有“梦里不知身是客”[3]的恍惚。但与中国最底层民众的不断接触,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为之服务、捍卫其权利的,最终说来就是他们,而不是抽象的正义。他们是和我们父母一样都或多或少遭受一些时代浩劫和生活挫折的人,一些更关心自己生存的人,一些似乎没有所谓“远大理想”的人,一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放下我们“架子”,因为若干年后,我们可能就是他们其中一员。他们构成了城市、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风景,而法律援助的意义在于他们,效果也取决于他们。这是我的体验,未必准确。
还是要感谢一下同事们,没有他们的帮助、理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体验、感受。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你们,于是想起了《紫丁香校园》的歌词:你是无名星座,只有夜晚,我能够看清你,你能够看清我。无需诉说南风吹落的欢乐。晨曦伴随着寂寞,守护着无边银河。每一个义联人都像是无名星座,在夜晚默默的闪烁。未来,我相信,即使经历再大的困难之后,每当红轮西坠繁星满天时,我们仍然会看到“银河边”那一个个无名星座。
还算是个维权实录么?感性的思考中还带了不少粗鄙的妄言。但替代公文般的写作的不仅仅是在若干年后“柔弱的想起”一个叫义联的地方,还有对公益事业未来的憧憬。
祝福义联!祝福义联的同仁!
周文政
2011年开学的日子 于北京
本图文系义联原创,版权归原作者及义联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杨藜)
- 上一条文章: 泣血十一载,维权路上独行侠(续)
- 下一条文章: 走在工伤认定的漫漫长路上(一) ———小霞工伤认定前奏,劳动关系确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