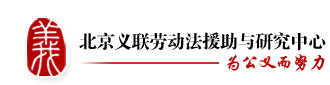农民工何时圆上“中国梦”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我国目前有农民工超过2.5亿人,约占城镇实际劳力的50%以上。农民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与付出相比,农民工所获甚微。职业尊严和生存保障的缺失,让他们成为这个国家最边缘化的群体。我和义联同仁们在为农民工长期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中,也深刻地感受到农民工面临的诸多困难,这些困难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这些困难中首当其冲的是讨薪难,一年干到头,却因为讨不到钱无法回家过年。讨薪难,难在三个方面:一是找人难,这种情况在建筑工地非常常见,农民工只知道包工头是谁,却不知道给谁干活,年底讨工资的时候,包工头跑路,农民工找谁谁都不认,只能干着急;二是举证难,农民工大多签不了劳动合同,工资都是口头协商,老板不认账,农民工举不出证据,法律就不能支持,自己只能吃哑巴亏;三是结算难,现在社会对于低端劳动者的需求量大,农民工的流动也比较频繁,老板为了保证来年能够正常开工,故意不给结算工资,或者只结算一部分。根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劳动维权研究报告(2007-2012)》,劳动争议中有50.09%涉及到劳动报酬争议。劳动报酬权利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而“欠债还钱”不仅是基本的法律规则,更是道德底线,农民工连工资都讨不回来,令人叹惋。
第二个困难是工伤、职业病维权难。农民工遭遇工伤、职业病事故,能够及时得到赔偿是少数人的幸运。更多人遭遇的是不幸,他们没有办法认定工伤、没有办法得到职业病诊断,没有办法得到及时救治,结果小伤拖成大伤,大伤直接拖死。工伤、职业病维权,难在三点。一是举证难,农民工在受伤后基本都面临被单位抛弃的命运,他们大都没有办法证明劳动关系,因而也无法按工伤处理。二是时间长、成本高。因为法律程序繁琐,一个工伤事故拖上两三年解决完是常事,有拖上十多年也没有认定工伤的,让一个农民工耗上几年的时间打工伤官司实在是耗不起。三是赔偿难。官司打完了,老板的公司也没了,最后农民工拿到的只是一纸空的判决。虽然《社会保险法》已经出台了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制度,可是在实施中形同虚设,制度实施一年多了,工伤农民工几乎没有享受过先行支付待遇。
三是子女上学难。农民工在城市打拼,希望和自己的子女生活在一起,也希望帮助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可是,农民工子女却难以在城市享受同等的义务教育权利,面临歧视和现实障碍。一是难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公办学校只招收本地户籍的适龄学生,对于外地学生则规定了苛刻的条件,高门槛让农民工子女对公办学校无望,只能转向打工子弟学校。二是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导致农民工子弟在城市上学更加困难。这导致了大量儿童留守在农村,或是流连在城市,成为“混混”。三是难以享受公平的教育,农民工子弟获准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即使学习成绩好也难以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四是升学难,即使农民工子女在获得中、小学上学机会,可是他们却面临诸多限制难以在异地参加高考,升学无望。
四是城市生活难。近几年,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房价、物价一路飙升,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可是,农民工的工资却难以见涨,即使略有增长,也赶不上物价的增速。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他们所为之努力的城市,已经渐渐容不下他们的生存。
五是城市融入难。对于农民工而言,城市是他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地方,俨然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可能回到农村,“农民工回老家养老”其实是城市人的臆想。由于农村经济的相对凋敝,以及文化生活的匮乏,许多农民工已经不适应长期留在农村老家生活。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渴望融入城市,可是却不被城市所接纳。农民工融入城市难,有几个方面:一是户籍限制,农民工从出生之日就被贴上农民的标签,除非通过考学改变命运,一辈子都背着农民的身份,户籍界限难以打破;二是社会保障,农民工因为身份的限制,在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水平、社会服务资源分配等方面,都与城市居民有着巨大的差别;三是面临可持续发展难题,农民工在城市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在技能提升上缺乏机会,在失业时,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给本地户籍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或就业培训服务,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在农民工面临的这些困难中,讨薪难和工伤、职业病维权难本不应该出现。这些权利已经早在十年前,甚至更早就被法律和各个层级的规定所承认。但这些困难时至今日仍然像一座巨石横亘在世人面前,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以讨薪难为例,各级领导的重视、各个部门的配合、各项法律制度的改进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讨薪难题(2013年春季本刊刊首语有详细阐述)。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根源之一就在于农民工缺乏自身群体的利益代言机制,没有形成和资方相抗衡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政府再多运动式的检查和呼吁,再多长篇累牍的法律规定,再多普法宣传教育的投入,再多政府机构的设立,也会消解在普遍而弥散的用人单位违法中,消解在政府部门的选择性执法中,消解在成年累月的仲裁和诉讼程序中,最后化作农民工的一声叹息。如果农民工可以同资方有足够的谈判力量,那么欠薪,又如何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呢?
根源之二在于政府机构的部门利益导向。农民工维权的法律程序繁琐,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部门对利益的划分。农民工为了证明劳动关系,要先做劳动仲裁,再经历一审、二审。劳动仲裁程序前置完全就是浪费社会成本和司法资源,给农民工带来更大的障碍,却多年未被废除。职业病问题,本是最基本的劳动保护问题,却生生被拆到了安监、卫生、劳动三家行政部门,让农民工在每个部门的程序中不停地等待,甚至最后还要再到法院。其次,政府部门为维护自身利益往往采取不作为。例如,人社部门就普遍地以各种理由拒绝工伤农民工的工伤待遇先行支付申请。各部门的互相推诿也是造成维权难的原因。笔者自2010年以来就开始关注并深度参与《职业病防治法》及配套制度的修订,2009张海超“开胸验肺”对世人的警醒拉开了这场修法的大幕。然而,经历了数以百计的立法研讨、调研、论证,最初旨在解决职业病诊断难的立法初衷,却在各部委的推诿下,给本来就很困难的职业病诊断程序,增加了劳动关系认定和安监部门调查两个前置程序。如果具体落实法律的各政府部门不以公共利益出发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或者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再提上议事日程,则再好的法律都会在执行中被层层消解掉,农民工的基本法律权利的实现也只是个白日梦。
如果农民工只是实现自己的基本法律权利就如此困难,迈向其城市新公民的路途可以想见会更加步履维艰。例如,曾有“农村土地换城市社保”的说法,要进一步剥夺农民工的权利。要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城市新公民身份的转化,需要政府真正改变GDP为导向的指挥棒,更多地关注公民的幸福和尊严。
要解决上述的五个难题,笔者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从以下几个方面付诸行动:
一、增强农民工群体在立法过程中的利益代言机制。立法机关应该将立法过程最大化地向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公益机构开放,制度化地邀请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公益机构等组织参与到立法的调研和论证过程中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公益机构等组织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工群体的问题,把现状和建议反映到地方和中央的立法决策机构。
二、增强农民工的谈判力量。将集体谈判制度引入农民工群体,加强工会的代表作用;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公益机构更多地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和社会工作服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对农民工的帮扶给予更大倾斜。
三、推动机构改革,简化农民工权益的主管归属机关。例如,安全生产与监督局在多国均为劳动部的下属部门(我国在机构改革前也是如此),建议劳动监管职能一体化,所有与劳动监管相关的职能统一划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四、简化工伤、职业病和其他劳动争议的法律程序,废除劳动争议仲裁这一前置程序,将职业病诊断、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三段程序整合为一。
五、给予农民工更切实的法律诉权,保障执法落实到位。对于行政部门不作为的情况,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应明确给予劳动者畅通的复议和诉讼渠道。对于部委和基层部门通过制定规章等途径减损农民工权益的情况,应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防治部门利益扭曲法律规定。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我们通过“剪刀差”实现农村对城市的补贴,通过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现在,社会反哺农村、反哺农民工的时刻了。愿农民工们早日实现中国梦!
文章原载于《团结》杂志2013年第4期,此处略有改动。
- 上一条文章: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 下一条文章: 中国式养老·延长养老金缴纳年限能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