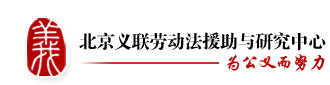【法治周末】朱茂林律师接受采访行政诉讼改革呼之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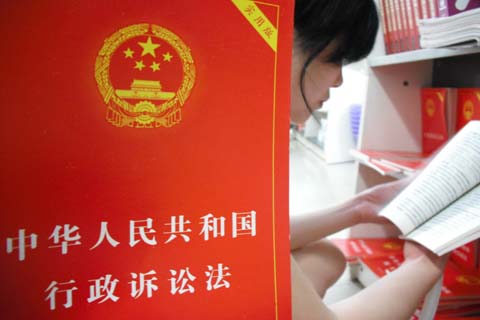
最高人民法院试行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的探索,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浙江丽水的改革效果也很明显。但如何保证法官不受行政干预的影响,仍是一道待解的难题。
“立案难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难点之最,因为不能立案即意味着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因而原告只能在若干行政机关(包括信访部门)之间来回奔走。”王优银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民告官”涉及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切身利益,后者往往就此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各方关系,律师、法院都在被“协调”之列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也被民众形象地比喻为“拿鸡蛋碰石头”。这种比喻既贴切当前的实际情况,也反映出了民众对“民告官”现状的无奈。
这种无奈不仅停留在民众中间,一些身处行政审判岗位的法官也有相同的感受。
一位资深行政审判法官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的相关座谈会上坦露心迹:“从事行政审判十余年,越干越感到困惑,因为行政审判司法公信力越来越低。”
相关数据和案例表明,现有行政审判体制下,抵制外部干预乏力。
一方面,原告的诉权难以得到保障,一些案件在各种干预之下无法立案;另一方面,立案之后,法院的独立裁判也受到影响。
“行政审判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民告官”案件日益增多
“民告官”的基石——现行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颁布、1990年实施以来从未有过修改。如今,延续了24年的行政审判体制,其改革终于提上了日程。
据财新网报道称,两个月后,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将初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可以相佐证的消息是,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分别在北京和福建主持相关座谈会,调研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方案,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支持。
上述两地的座谈会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主持,参加者包括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各省高院分管行政审判工作的领导以及行政法学界学者。
“民告官”制度,最早在我国试行的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以约束强大而极具扩张性的行政权力。1990年,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后,“民告官”案件日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公报显示,自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到2012年的22年间,全国法院一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91万余件,年均83168件。
这个数据,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民事诉讼案件和刑事案件来说,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但是纵向比较起来,近年来“民告官”案件虽有增有减,但还是保持在一定的数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告官”案件?
来自据称是中国首家专业从事行政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的王优银律师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转型期引发“民告官”的事件越来越多,在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移民搬迁安置、公安行政执法、土地行政执法、企业重组改制破产等诸多问题上,地方及有关部门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事件层出不穷。
二是民众法律维权意识在增强。尽管“民”在不得已告“官”时,压力大阻力更大,但“民告官”却是公正处理官民关系的一种非常透明、更让人民信服的方式。
王优银介绍,目前行政案件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领域,征地拆迁造成社会矛盾激增,因此此类案件在增多。
此外,诉讼成本的降低也是行政诉讼日益增多的原因之一,王优银表示。
按照国务院公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行政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纳: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每件交纳100元;其他行政案件每件交纳50元。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朱茂林律师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民告官”案件数量和关注度的上升,深度折射了“官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转变。随着我国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传统的“父官子民”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在遭遇侵权时,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民告官”有形无形干预多
媒体曾用5句话概括“民告官”的现状:民告官,起诉难;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难告赢;民告官,执行难;民告官,代价大。
律师王优银则用四大难来总结“民告官”的现状:立案难,依法管辖难,公正难,违法判决纠错难。
有关数据显示,行政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全部案件当中比例非常小,约占2%。
“立案难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难点之最,因为不能立案即意味着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因而原告只能在若干行政机关(包括信访部门)之间来回奔走。”王优银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民告官”涉及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切身利益,后者往往就此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各方关系,律师、法院都在被“协调”之列。
迫于各方面压力,很多律师往往不愿意代理行政诉讼案件。
马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国行政案件长期徘徊在10万到12万件,原告胜诉率不到10%,审判效果和质量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方式对行政审判加以干预。”
目前行政诉讼中“民”的胜诉率不足三成,某种程度上就与一些地方政府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有很大关系。
不仅是对案件干预,更为极端的是针对法官本身的措施。
媒体报道说,东北某省法院一位行政庭的领导准备到北京出差,还没走到火车站却被紧急叫了回去。原来在此之前该省某基层法院的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判决基层政府败诉,当地政府遂以法官涉嫌违纪为由,当地检察机关介入案件调查。政府部门要求上级法院启动再审,否则将进一步采取措施。
最近几年,全国法院系统的案件之中,申诉案件比例为整体案件数量的1%至2%,但行政申诉案件却占到全部申诉案件的19%左右。这类申诉中,行政机关申诉的案件极少,99%的行政案件申诉人都是普通百姓。
“数据说明行政审判的公信力不高,完全成了倒金字塔型。”上述曾在相关座谈会上坦露心迹的资深法官说。
王优银表示,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有些法院在审案过程中偏袒被告、动员原告撤诉、甚至擅自变更被告等不正当行为并不鲜见。
同时,间接诉讼成本过高也受到学者和律师的关注。
虽然行政诉讼的直接成本较低,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诉讼的间接成本过高,“这个成本主要指的是经营环境成本高。”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她举例,比如某企业因发现与其长期打交道的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违法而起诉,这些作为监管机构的行政机关,在输了官司后不能正确认识诉讼权利,那么对于作为原告的企业来说,未来的经营环境就会恶化,这就导致行政诉讼的间接成本过高。
如果说执行是法律诉讼的难点,那么行政诉讼中的执行就更是难上加难。
媒体曾报道过全国首例农民状告县政府行政不作为案,法院终审判决县政府履行职责,县政府却作出维持现状的处理决定。这种“作为”无异于“不作为”。无奈之下那位农民只好再次将县政府告上法庭。
由于法院缺乏强制执行手段,很多时候“民”即使赢了官司,也难以从“官”那里真正讨回公道。
一位资深法官说,“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初,有的地方判处行政机关改变行政行为,最初能达到整体受案数量的60%左右,后来逐步降低,现在包括各种方式,加起来能让行政机关改变的也不到10%。”
破难题出路在探寻
法院系统也一直试图抵制类似干预。这可以从法院近些年主张的审判模式改革当中略窥一二。最著名的当属“行政案件异地交叉审理”和“相对集中管辖”两种模式。
2002年7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推行“行政案件异地交叉审理”。同年9月,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启动了“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
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试行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的管辖制度。
丽水的改革效果很明显。一方面,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上升,2006年和2007年丽水全市一审行政案件数分别是110件和111件,实行集中管辖制度后的2008年和2009年增加到191件和201件,上升了74%以上。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败诉率也明显提高,2008年丽水市行政机关败诉率为26.9%,居浙江省第一。2008年集中指定管辖的56件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的有20件,行政机关败诉率达35.7%,远远高于全市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机关的败诉率。
总体而言,这两种做法仍是权宜之策。马怀德说:“基层法院的案件即便提级到中院审理,但现在很多地方县(区)委书记是市委常委,县(区)里边的行政案件,如果书记给中院院长打招呼,中级法院仍然很难有能力排除这样的干预,如果还在老的系统内进行改革,我觉得出路不是很大。”
那么,在“民告官”案件中,如何保证法官尽量不受行政干预?
学者王敬波建议打破行政区划,使行政审判管辖体制与行政区划相脱离,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
律师杨应军也建议尽快摆脱法院在人、财、物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局面,提高行政诉讼的受案审级或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以提升司法权威。
执行难在民与民的关系中就是一个难题,在官民关系中更为突出。杨应军主张,如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不执行行政判决,应对其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其挑战司法权威的成本,从而使其真正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原链接: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3306
(编辑:谢越)